蘇亦一直呆在北大,直到馬世昌離開兩天之后,才坐上南歸的列車。
不是他不想繼續待在北大,而是盤纏有限,錢倒是有一些,但糧票卻是不夠的,好在,宿先生還刻意分他一些糧票,就算如此,也是不行,因為,他不是一個人,陳飛也跟他一起留在北大。
不是陳飛留戀北大,而是他不放心蘇亦單獨返程。
他把蘇亦安全送來北大也要安全的送回家。
有始有終。
盡心盡責。
蘇亦就算再不舍,也只能夠在北大待一周。
再多,不行了。
這兩天,蘇亦也沒有閑著,還是翻書,主要啃的就是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跟《斗雞臺溝東區墓葬》、《洛陽燒溝漢墓》是周秦墓葬以及漢代墓葬的開山之作一樣,《白沙宋墓》也是宋代漢墓考古的開山之作。
這三本書都是考古發掘報告的典范之作。
都要細讀。
尤其是《白沙宋墓》更是重中之重,誰讓這本書的作者是宿白先生。
而蘇亦又報考他的研究生呢。
前世,蘇亦也看過《白沙宋墓》,確切來說是翻過,里面很多東西是看不懂的,里面的注釋涉及到的文獻太多,如果沒有一定的文獻基礎,讀起來就非常的吃力。
這是一本注釋比正文還要多的考古報告。
現在讀起來嘛。
就沒有那么吃力了。
比如,注釋涉及的《史記》蘇亦讀過、《漢書》蘇亦讀過、《魏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明史》等二十四史,蘇亦都讀過。
其他的,比如《四部叢刊》里面的《書經注》、《夢溪筆談》、《唐律疏議》、《圖畫見聞志》等蘇亦也讀過。
甚至,《畫鑒》以及米芾的《畫史》他都讀過,畢竟他前世本科讀的就是美術史。
當然,大部分他文獻他是沒有涉略的。
比如,周密的《志雅堂雜鈔》、徐鉉的《稽神錄》等他聽都沒有聽說過。
所以說讀書的廣度以及精度上,他是沒法跟宿白先生比較的。
也確實比不了。
兩人同屬的時代不一樣。
所受到的培養方式也不一樣。
蒙學讀物不一樣,文獻功底不如老一輩的先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相比較前世,現在的他,文獻功底確實提升了不少,至少《白沙宋墓》是讀懂了。
再說,文史樓的閱覽室里面資料不少,翻書的時候看到感興趣的注釋,就可以借閱原著。
這就是北大的優勢。
這是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
然而,蘇亦終究還要離開。
那天晚上,馬世昌過來串門的時候,沒少跟他說關于《白沙宋墓》出版的事情。
因為這本書圖片太多了。
征引和手繪了大量建筑、繪畫、器物作為插圖。
沒法子,這也是宿先生撰寫發掘報告的特色。
誰讓他具有相當不俗的手繪功底呢。
不過根據馬世昌的說法,里面的手繪也不全是宿白先生畫的。
宿先生也只是手繪了寫生一小部分,真正有需要的建筑圖、斗拱、平、剖面圖、都是請莫宗江先生畫的。
莫宗江是營造學社成員,建筑史學家,國徽的主要設計者之一,也是梁思成先生的弟子。
對古建研究有著深厚的造詣。
五十年代北大考古專業開課的時候,就曾經請莫宗江先生過來教授手繪課程。
實際上,幕后的工作不僅僅有莫宗江。
臨摹壁畫和拍攝彩色照片的有葉淺予、董希文、劉凌滄、林崗、楊之光、潘絮茲和彭華士諸先生,莫宗江先生為白沙一號墓繪制了墓室結構透視圖,余鳴謙先生參加測繪了白沙一號墓的平面、仰視、立面和剖面圖。
這些先生都是牛人。
董希文就不說了。
宿白先生的素描老師。
油畫大牛。
所以才有人說,這項考古發掘和各種記錄工作在人員的組成上,可以說是集考古、藝術界之精英,在中國現代考古學史上實屬罕見。
這些幕后的故事,馬世昌不說,蘇亦肯定是不知道的。
因為他前世讀《白沙宋墓》的時候,已經是17年的最新版本的,里面精美的印刷以及插圖,跟57年版本已經有不小的改變。
當然,內容是不變的,正文、注釋都沒有改變。
這本書能夠成為中國歷史考古學田野報告的奠基和經典之作,也是有其道理的。
奈何,蘇亦前世讀研的時候,對歷史考古學研究不深。
當然,也不是沒有讀過。
《白沙宋墓》是專業必讀物,想要了解中國古建,《營造法式》,宿先生的《中國古建筑考古》都是必讀物,不過這個時候,古建筑考古這本書并沒有出版,甚至,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古建筑考古都不能夠成為一門學科,只能算是考古關聯方向。
他前世學公眾考古,蘇亦寫公眾號推文的時候,會專門作一些考古專著推送,推送的書基本上都會讀過,但也都是泛讀,很難精讀。
現在重讀《白沙宋墓》,又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而且,這本書還是宿先生親自送給他的,里面還有宿先生的親筆簽名,珍貴的程度可想而知。
不細讀,良心有愧。
甚至,里面涉及到不少宋代墓葬元素。
甫道壁畫馬。
開芳宴。
屏心畫水波紋。
婦人啟門。
人墓祭儀和買地券。
紙明器。
唐宋堪輿書。
宋皇家選塋地。
等等。
這玩意,要是后世寫盜墓小說的作者隨便翻看然后照抄,都可以營造出非常精美的畫面感了。
所以,蘇亦都有一個荒唐的想法,要是讓宿先生去寫盜墓小說,他會寫成什么樣?是不是畫面感十足?
或者寫著寫著,最后就變成考古報告了。
估計,后者的可能性最大。
一想到這,蘇亦就覺得荒誕。
宿先生怎么可能去寫盜墓小說,就算是小說,宿先生也不可能寫。
不過考古界的前輩,有沒有人兼職寫小說的?
肯定是有的。
比如大名鼎鼎的考古界前輩童恩正先生,后世,堂堂考古界的大牛,川大前考古學系主任,百度百科卻冠于“作家”來分類,可想而知童先生影響力。
甚至,童先生還有中國考古小說第一人的稱號。
當然,這些后話。
重點,現在對于蘇亦來說,重點還是看書,而不是寫書,更不是寫小說。
甚至,當天晚上馬世昌離開的時候,不僅讓精讀《白沙宋墓》,還讓他好好學日語。
用馬世昌的話來說,既然你的英語那么好了,就需要開始學二外了。
當時,馬世昌說得輕描淡寫,理所當然,讓蘇亦哭笑不得。
……
馬世昌離開的時候,還跟蘇亦分享早年宿先生教授秦漢考古的經歷。
馬世昌說,五十年代,考古專業初創的時候,當年條件有限。
上課,不僅沒有教材,連講義都沒有,甚至資料都少得可憐。
蘇秉琦先生授課還可以講他斗雞臺的經驗,宿先生完全就沒得講。
早年,白沙宋墓都沒發掘。
沒法講,怎么辦?
當然是用別人的成果。
國內,沒有,就用國外。
這個時候,利用曰本人的成果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宿先生教授秦漢考古的時候,就經常利用曰本人的成果。
主要就像曰本人在朝鮮平壤附近挖了很多漢墓,那些漢墓很了不起的,都很大,很完整,后來都出了很厚的一本報告,宿先生當年給講學生這些報告。
而這本報告就是《樂浪》,
這也是大部分第一批考古專業的學生對于西漢墓的最初接觸到的資料。
關于曰本人在平壤發掘的西漢墓,叫什么,馬世昌也作了相關的說明。
也就是樂浪古墓。
“樂浪遺址的發掘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事件。”
“東漢王盱墓是朝鮮樂浪郡城遺址之一,1925年由東京帝大文學部發掘,其時,朝鮮為曰本吞并統治。”
“樂浪古墓應該算是發掘比較早的漢墓了,要知道直到1972年長沙西漢馬王堆發掘才被發掘出來,比樂浪郡王盱墓要晚47年。”
幸好老馬同學不是憤青,不然,擱后世,跟棒子爭論,用樂浪郡的例子,就可以劈里啪啦的扇他們的臉了。
因為,棒子最喜歡玩申遺那套,然后用來證明的他們的歷史久遠。
忽悠游客。
用馬世昌的話來說,就是,“朝鮮樂浪郡,是西漢漢武帝于公元前108年攻滅衛氏朝鮮后在朝鮮半島設置的漢四郡之一,治所在朝鮮縣(今平壤大同江南岸),管轄朝鮮半島北部,公元313年,被高句麗吞并。”
樂浪古墓的發現,證明了朝鮮半島最初確實是屬于漢朝的統治。
至于高句麗,一直以來都被韓國學者歸類于他們的祖先。
如果研究東亞史的話,高句麗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馬世昌也沒有贅述。
實際上,馬世昌分享宿先生利用曰本人成果的例子,不僅僅是《樂浪》發掘報告。
馬世昌說,“當年,宿先生也介紹給我們,曰本人在張家口一帶,還有在邯鄲他們做的找過的城,有一個報告,他就介紹我去看這些東西,我覺得收獲挺大,因為那個時候,像現在的文物考古的內容,中國人沒做,主要是靠曰本人做的,宿先生讓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從曰本人的工作來看漢墓整理的情況。”
當然,利用曰本的成果,也不是每一個北大考古專業的老師都可以的。
首先你得懂日文。
恰巧,宿先生的日文就很不錯。
這也是跟他的求學經歷有關。
他當年就讀的是“偽北大”,除了來自原北京大學與北平大學留守的教授外,還有相當一批偽北大教授來自日本,是該校教授群體非常顯眼的一個特征。
6個學院中農學院、醫學院與文學院的日籍教授較多。
恰好,宿先生讀的就是文學院。
所以,宿先生的日文相當好。
這也是為什么宿先生可以在云岡石窟問題上打臉曰本學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是日文不好,看不懂日文文獻,怎么可以他山之石可攻玉。
當時,馬世昌就跟蘇亦說,“在這以前,我們講的秦漢考古沒有材料,講來講去,講曰本人的,把曰本人的拿來看,不過當初曰本人做的工作,說實在的比起我們現在做的工作要差好些,不如我們現在做的正規。”
說了,宿先生的例子。
馬世昌又跟蘇亦分享了俞偉朝老師的故事。
因為俞偉朝先生就是考古專業最早的一批學生之一。
當年,他們看的書,大部分沒有中文版,只有日文版,因為只有曰本人做過研究。
像《支那古銅精華》大部分的銅器都是曰本人印的,還有曰本有名的梅原末治他寫了好幾本書,這都是曰本人弄的。
曰本有銅鏡斷代的書,中國沒人研究,曰本人走在了前面。
馬世昌說,“俞偉朝老師,當年是北大博物館專修科的,當時條件不錯,還有一個開架的閱覽室,日文書全都放那里,所以俞偉朝老師看的特別多。實際上,俞偉朝老師他的學術修養非常好,懂的東西非常多,瓷器、剔紅、刺繡這些俞偉朝老師都懂。”
當時,蘇亦就問,“俞偉朝老師涉略也太廣了吧,連刺繡都懂?”
馬世昌笑,“其實,俞老師跟沈從文先生的私交非常好,沈先生不僅是個大作家,也是文物學專家,對刺繡,服飾方面有很深的研究。”
沈從文先生解放后從事中國紡織服飾考古研究工作,這一點,蘇亦是知道的。
他當年在美院讀書的時候,會看過一些美術史的書,沈從文先生編寫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也看過。
基本上后來美院或者服裝學院關于服裝史的教材都是在沈從文先生的研究基礎上拓展的。
然而,他跟俞偉朝老師私交甚好,蘇亦還真不知道。
不過想想也正常。
早年,北大專修成立,就曾經聘請了沈從文當老師,當時,對方恰好調任歷史博物館。
一想到日后,俞偉朝老師就任歷博館長,蘇亦就釋然了。
馬世昌跟他舉例、宿白先生、俞偉朝老師的實例。
并不是為八卦。
而是想實實在在的告訴他,學習日文是有用的,對學術研究只要好處沒有壞處。
日語的作用,也不需要老馬同學來強調。
就算不用來看文獻,看小電影作用也不小。
所以,蘇亦返回廣州的時候,行李之中除了《白沙宋墓》這些考古發掘報告之外,還有不少的日語入門專業書。
這樣一來,之前借來送許婉韻的三輪單車就再次派上用場了。
不過,這個時候,馬世昌也已經返回敦煌,就連錢立群錢教授也已經提前回去。
這種情況下,蘇亦能夠找的人,也只有本科生了。
這個時候,之前認識的文學院大一新生,王先勇的作用也體現出來了。
都是人家的小師兄了。
使喚起來小學弟,問題不大。
于是,在浩浩蕩蕩的三十多個小時以后,蘇亦跟陳飛開始拎著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出了廣州站。
……
……
注:《樂浪》,原田淑人,田沢金吾: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印,1930年。
樂浪郡遺址的發掘成果《樂浪》一書,被稱為“學術界之鴻寶”、“考古學上一大著作”、“偉大之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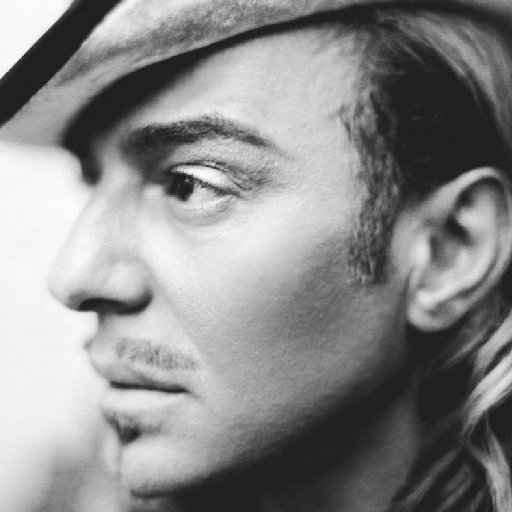
莫韃
文獻這部分應該有點枯燥,里面涉及到太多的內容,也有蠻多有意思的小故事,但寫出來,感覺不太行,鋪墊太少,劇情沒起伏,下章,應該是新劇情的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