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許迦的一席話就如那春風,在同學們心里飄起羽毛般輕盈的雪花兒。
不是縱橫捭闔的言論,卻不得不令人欽佩。
“迦姐,愛您!我真的好幸福!”
傅汀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拽住許迦的校服衣角,雖有夸張的成分,但不掩婆娑淚眼里的幾分真情。
許迦嫌棄地甩開他的爪子:“第二次了,矯情。”她剛剛的舉動實際是有些魯莽的,從此不可避免成為小應心中的一根刺。這下再次看到傅汀掉眼淚,也是有些無奈。
傅汀也不惱,笑了笑收回手,湊到自己這位冷冰冰的同桌邊上。
“嘿,林禎,你知道嗎?她倆死活不讓我一起去醫(yī)務室。雖說要找人請假,怎么不讓趙眠回來呢?”傅汀這表情十分滑稽。
“嗯。”林禎應答地有些敷衍。
許迦跟趙眠又湊到一塊去了,從林禎這個角度正好能看到趙眠含情脈脈的眼神。林禎視線左移,不想被許迦頸間一抹瑩白晃了神。
耳畔的傅汀還在喋喋不休。
“還有啊,剛剛我假睡的時候,看到許迦在摸趙眠的肩。還有之前許迦腿根本沒事,卻跟趙眠摟著去的醫(yī)務室……”
“不是早說過許迦喜歡趙眠嗎?”林禎似乎是聽不下去了,低吼道。像是不堪禁錮的困獸在咆哮。
傅汀卻慫了,他想不到林禎這音量還不小啊!完了完了,前面兩位該聽到了。
許迦確實聽到了,說實在她跟林禎自返校當天之后再無交流。
那次徒步,她更是感受到林禎對自己深深的惡意,現(xiàn)在,她不想再念及舊情了。
“林禎,你說什么?”許迦琥珀色的眸子里面沒有了小太陽的萬丈光芒,像是泛著月光的湖泊,水波微微蕩漾。
林禎連多余的表情都不想給,只冷淡道:“怎么,你喜歡趙眠還不夠明顯嗎?”
“哪種喜歡?”許迦語氣有些羞惱,調(diào)子卻是婉轉的。
林禎一副跟她一句都不想多說的態(tài)度。他像是不耐煩地回答道:“這年頭有些女的非要喜歡女的,跟我們搶。我就想問問,你們怎么繁衍后代?”
林禎低頭干自己的事。
傅汀很慌,他倒也不是覺得林禎說的都是錯的,但很明顯語氣不太友好。印象中許迦曾經(jīng)說過她不挺認可同性戀,再說她似乎真的喜歡趙眠啊……林禎今天是怎么了,他怎么一點面子都不給。
噢,傅汀恍然大悟,林禎一定是不接受同性戀的!誒,好好的一個小組,就因為一個關于同性戀的觀點產(chǎn)生分歧。
許迦真的被氣到了,一口氣憋在喉嚨不上不下的。她一直以為自己的心智在成長,不會輕易卸下偽裝,可是現(xiàn)在她一點兒也不能接受林禎這樣的言論。
“別跟他置氣,不值得。”趙眠扯了扯緊繃著的許迦,小聲說。趙眠不喜歡林禎,從看到第一眼起就沒有好感,她總覺得林禎是個心機很重的男生。
許迦這一次沒有聽趙眠的話,因為林禎觸犯到了她的底線。
她不是一個任人宰割的羔羊,不會對他人的惡意一次次退讓。
“林禎,我告訴你。第一,同性戀是否存在跟你能不能找到對象少混為一談,別給自己單身找理由。第二,繁衍價值確實是擇偶的重要標準,但絕不是唯一標準,因繁衍后代而結合的婚姻是何等膚淺?第三,關于同性是否能夠繁衍后代,請不要讓貧乏的知識限制了想象力。第四,我喜不喜歡趙眠,跟你林禎,沒關系!”
林禎頭都沒抬,沉聲道:“嗯,我跟同性戀傾向的人巴不得沒關系。”
這句話只有許迦聽到了,她自以為剛剛那一席話自己能夠扳回一城,卻被林禎用這樣侮辱的方式輕飄飄地推了回來。
許迦自己自然不是真的有同性戀傾向,或許受到網(wǎng)絡文學作品的影響,她很尊重同性戀。
她也知道老一輩的人大都無法理解為什么同性之間會互相喜歡,這免不了受到時代的影響,但包括她的長輩,雖不接受自己的孩子喜歡同性,至少對待同性戀有基本的尊重。
可眼前這個同齡人,居然這樣惡語相向,怎么會有這樣自我的人,這樣惡劣的人?
許迦回想起剛認識林禎的那段日子,雖然這個后桌總是挖苦她、嫌棄她,但他有好幾次為她一聲不吭地解圍。他們雖然交流不多,但是她曾經(jīng)以為他也是想要跟她成為朋友的。
那時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后來感覺他的城府也是深的,才有了保持距離的想法。
直到此刻,許迦才明白自己在林禎眼里不過是一個任他為所欲為的玩具。
初時一時新奇,再見棄若敝屣。
許迦的馬尾辮扎的不是很緊,風一吹便散落了幾根烏黑的發(fā)絲,輕柔地拂過她柔嫩的臉頰。
一根細細的泛著金色光澤的發(fā)絲悄悄地鉆進她半瞼的杏眼上鴉羽般的濃密睫林,有些癢癢的。許迦眨巴幾下那雙迷人的眼睛,只想擺脫四處搗蛋的頭發(fā)絲兒。眨著眨著,她不但沒有得逞,似乎還被頭發(fā)絲兒纏得更緊了,像是被膠水黏住了似的,怎么愈發(fā)難受了。
許迦不得不指節(jié)微曲,指尖試探的觸碰了一下自己的眼框,有一點沁涼。
噢,難怪,睫毛是潤潤的,把幾根頭發(fā)絲兒困在一方溫澤。
傅汀不忍地搭上林禎的肩:“喂,你把我迦姐快惹哭了!”說實在,傅汀看到許迦這樣子很難受,覺得許迦永遠不該是這樣的。梨花帶雨本該是角色,可他寧愿一輩子看不到。
許迦的琥珀色眸子此時又淡了幾分,很輕很薄,好像精致易碎的琉璃杯。下眼眶像是一泊清潭,水光浮照,氤氳動人。
林禎沉默著扒掉傅汀的手,毫不拖泥帶水地離開教室。明明還是上課時間啊。
林禎朝著那架光線昏暗的樓梯走去,步子邁得越來越大。他在那個熟悉的兩個人對峙的轉角處停下。
林禎更個人倚靠在墻角,身體失去重心般一寸一寸地下滑。他最終蹲在墻角,雙手緊緊抱著頭。那是一雙青筋隱隱暴起的手,清瘦纖長,白到病態(tài)。一只手鋒利的指甲甚至嵌進另一只手,滲出了血絲,他毫無知覺。
明明該感到解脫的,籌備許久,今日終于走到最后一步,他再也不用為那個毫無共同語言的女孩憂心忡忡。
她哭什么?以后我離她遠遠的該開心的。跟周漠站在一起,挺配的。
不敢看她,怕自己潰不成軍。
一個沒有心的人,怎么會疼?
可他哭了。
哭得沒有眼淚,沒有聲音。
看到許迦要哭不哭的倔強模樣,教室里的趙眠很心疼。她二話不說,把剛買的一包抽紙拆好塞進許迦的手里。
趙眠很想抱住許迦,可是許迦面朝林禎,一點都不愿意動的意思。趙眠心中暗罵:太不要臉了。沒下限!
許迦的確很失落,不過并不是那種失去一個朋友、多一個仇敵的失落,而是對自己再度產(chǎn)生了懷疑。
好像總有人在她掉以輕心的時候給她當頭一棒,要她記得這個世界有多么陰暗,人心有多么不古。
自以為是個能把人看得透透的老江湖,不過是坐井觀天嗎?
她本來就不是好人。林禎不給她基本的尊重,也別指望她尊重他。
從此以后只有林狗,沒有林禎。
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
一刀兩斷,再無瓜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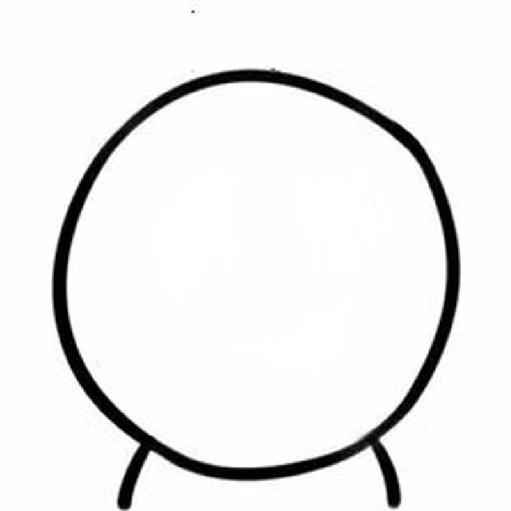
晝善
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