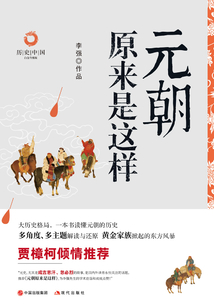
元朝原來(lái)是這樣(白金升級(jí)版)
最新章節(jié)
- 第59章 注釋
- 第58章 附錄2:成吉思汗的后宮佳麗
- 第57章 附錄1:成吉思汗究竟姓啥
- 第56章 遼夏金元諸朝對(duì)漢人性格的影響
- 第55章 皇帝被生擒,真心沒(méi)面子
- 第54章 元朝之外Ⅱ:巴布爾和他的莫臥兒王朝
第1章 建立元朝的蒙古人打哪兒來(lái)
中國(guó)兩千余年專制王朝歷史上,元朝(1271—1368年)是一個(gè)重要的朝代。言其重要,倒不是說(shuō)時(shí)間跨度,畢竟元朝只有九十七年的建朝史,而是因?yàn)樵瘜?shí)現(xiàn)了中國(guó)的大一統(tǒng)。元朝是中國(guó)歷史上首次由少數(shù)族群建立的大一統(tǒng)王朝。
元朝歷九十七年,共傳五世十一帝(汗)。若從1206年鐵木真成吉思汗(1162—1227)建立蒙古汗國(guó)政權(quán)開始,則共歷一百六十二年,傳七世十五帝(汗)。
蒙古汗國(guó)和元朝是前后連續(xù)、承繼的關(guān)系,其統(tǒng)治者皆出自鐵木真及其直系后裔。蒙古是從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一個(gè)族群。他們從哪兒來(lái)?
五千年前,中原以北的大片土地上,生活的族群是北狄。《山海經(jīng)》中“有北狄之國(guó)。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的記載。
北狄分化為“胡”與“東胡”。“胡”的傳承者是匈奴。“東胡”系族群在被冒頓單于領(lǐng)導(dǎo)的匈奴擊敗后,退至鮮卑山和烏桓山,分為烏桓和鮮卑二族。
東漢末年,烏桓被曹操征伐之后衰落,鮮卑崛起,在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主要分為段部、慕容部、拓跋部、柔然部、乞伏部等。
其中,柔然部與拓跋部建立的北魏長(zhǎng)期交戰(zhàn),互有勝負(fù)。
柔然被突厥族群擊敗后,分為南北兩支。其南支來(lái)到遼河上游老哈河、西拉木倫河流域游獵,成為契丹人的一支族源。其北支來(lái)到今外興安嶺以南地區(qū),被稱作“室韋”或“蒙兀室韋”,也就是后來(lái)蒙古人的祖先。
顯然,室韋與契丹同出一源,以興安嶺為界,“契丹之類,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hào)為失(室)韋”[1]。
蒙古人和契丹人血緣相近,口語(yǔ)大部分是相通的,相比女真人,關(guān)聯(lián)度要高得多,這也是后來(lái)蒙古人滅金之后,幾乎不用女真人,卻大量使用契丹人的原因之一。
中國(guó)東北地區(qū)重要的河流黑龍江,其上源為額爾古納河。額爾古納河在隋唐時(shí)期叫“望建河”,源于呼倫湖。隋唐時(shí)期,呼倫湖周邊住牧的“蒙兀室韋”[2],就是后來(lái)被鐵木真黃金家族率領(lǐng)的蒙古人。“蒙兀”是“蒙古”的同名異譯,在蒙古語(yǔ)中意為“永恒的火焰”。突厥語(yǔ)則稱“室韋”為“韃靼”。
后來(lái),蒙兀室韋在鐵木真始祖孛兒帖赤那的帶領(lǐng)下,西遷至今蒙古國(guó)境內(nèi)的克魯倫河和鄂爾渾河一帶游牧,逐漸以肯特山[3]作為其生產(chǎn)生活的中心地區(qū)。蒙兀室韋來(lái)到蒙古高原腹地后,與突厥、鮮卑、回鶻等不同族群相處、生活,也不斷接受著來(lái)自中原的文明的熏陶與滋養(yǎng)。
原先在呼倫湖以南住牧的韃靼人也進(jìn)行了西遷,與先期西遷的蒙兀室韋再次南北比鄰而居,逐漸形成了松散的“韃靼聯(lián)盟”。
唐末,土拉河、鄂爾渾河一帶的韃靼人被統(tǒng)稱為“九姓韃靼”,也就是后來(lái)金元時(shí)期的“克烈部”;陰山[4]以北的韃靼人被稱作“陰山韃靼”,也就是后來(lái)金元時(shí)期的“汪古部”;留在呼倫湖,未西遷的韃靼人被稱作“三十姓韃靼”,也就是后來(lái)金元時(shí)期的“塔塔爾部”。
中國(guó)古代北方少數(shù)族群稱謂變遷,正是其生產(chǎn)、生活方式和特點(diǎn)的寫照——同為游牧族群中相同或相近的一群人,無(wú)論分為多少部落,無(wú)論部落名稱叫什么,只要其中有一個(gè)或兩個(gè)部落在偶然的契機(jī)中迅猛發(fā)展壯大,成為大家公認(rèn)的領(lǐng)導(dǎo)者,那么整個(gè)地區(qū)族群的稱謂就都變成這一兩個(gè)“領(lǐng)導(dǎo)”部落的名稱了,匈奴如是,柔然如是,突厥如是,回鶻如是,韃靼如是,后來(lái)的蒙古亦如是。
因此,韃靼強(qiáng)大,使得當(dāng)時(shí)還比較弱小的蒙兀室韋被稱為“黑韃靼”。
唐朝開創(chuàng)了中國(guó)多族群同一國(guó)家的空前強(qiáng)盛的時(shí)代,大漠南北、中亞,甚至部分南亞地區(qū),都是大唐王朝的疆域。
在那個(gè)皇帝被稱作“天可汗”[5]的激動(dòng)人心的時(shí)代里,不同口音、不同語(yǔ)言、不同裝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方式,甚至不同種族的人們,共同生活在一個(gè)偉大的時(shí)代,共同生活在一個(gè)偉大的帝國(guó),共同勞作和奉獻(xiàn),他們書寫或努力學(xué)習(xí)書寫共同的文字——漢字,他們?yōu)閾碛幸粋€(gè)共同的稱謂——唐人而自豪。這樣的自豪感同樣及于韃靼人。
唐太宗貞觀年間,中央政府在大漠南北設(shè)立了行政機(jī)構(gòu)——燕然都護(hù)府[6],管理鐵勒、韃靼、回鶻等游牧族群。
10世紀(jì)初,鮮卑人后裔的南支,與“黑韃靼”有比較密切的血緣和族群關(guān)系的契丹人崛起,建立了契丹政權(quán)(后改為遼朝),他們將“黑韃靼”稱作“阻卜”。
遼朝倚仗立朝初年的赫赫兵威,以及與中原先進(jìn)文化融合的力量,不斷對(duì)阻卜用兵并征服了蒙古諸部,設(shè)府、衛(wèi)、司等機(jī)構(gòu)進(jìn)行管理。例如,遼景宗時(shí)在西北路招討司中置都祥穩(wěn)一職,鎮(zhèn)撫西北阻卜各部。遼圣宗時(shí)新建鎮(zhèn)州、防州、維州三座邊防要塞,橫亙于阻卜各部中,還任命大王、節(jié)度使等直接管理阻卜各部。
作為契丹人的“遠(yuǎn)親”,阻卜著實(shí)沒(méi)讓遼廷“省心”。他們動(dòng)輒就深入遼朝腹地進(jìn)行騷擾,往往是飛速地?fù)尳俸笥诛w速地消失。從遼圣宗時(shí)起,阻卜就時(shí)叛時(shí)服,遼朝曾多次派出大軍對(duì)阻卜進(jìn)行征討,消耗了不少國(guó)力,后來(lái)也是采取羈縻政策,將阻卜各部首領(lǐng)冊(cè)封為節(jié)度使,多加封賞,才算暫時(shí)安撫住。
那時(shí)的阻卜人,也就是蒙古諸部,還處在“人多散居,無(wú)所統(tǒng)一”的狀況。原韃靼中的“白韃靼”(后稱“汪古部”)被遼廷稱作“陰山阻卜”,肯特山一帶的被稱作“蒙古部”,呼倫湖到哈拉哈河一帶的被稱作“烏古部”(后稱“王紀(jì)剌部”“翁吉剌部”“弘吉剌部”或“弘吉剌惕部”),克魯倫河中下游的被稱作“敵烈部”[7],土拉河、鄂爾渾河一帶的被稱作“北阻卜”(后稱“克烈部”)。
對(duì)于強(qiáng)大的烏古部和敵烈部,遼朝在征服后,還專設(shè)“烏古迪烈統(tǒng)軍司”、節(jié)度使或祥穩(wěn)等職,進(jìn)行長(zhǎng)期監(jiān)管。原先相對(duì)松散但有一定部落聯(lián)盟特點(diǎn)的“韃靼聯(lián)盟”被瓦解了,客觀上為蒙古部的破繭而出創(chuàng)造了歷史條件。
12世紀(jì)時(shí),蒙兀室韋中的蒙古部子孫繁衍,氏族支出,漸分布于今鄂嫩河、克魯倫河、土拉河這三條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東一帶,組成部落集團(tuán),見諸經(jīng)傳的有乞顏、札答蘭、弘吉剌[8]、泰赤烏、兀良合[9]、合答斤等部落。
除了上述有著比較清晰的“蒙古”標(biāo)簽,明顯認(rèn)同蒙兀室韋的諸部,與他們當(dāng)時(shí)同在蒙古高原上游牧的,還有位于今天貝加爾湖周邊的塔塔爾部,位于貝加爾湖以東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兒乞部,位于貝加爾湖以西的斡亦剌部,這三部都使用與乞顏部等相同的語(yǔ)言,都忠誠(chéng)于原始宗教薩滿教。
還有三個(gè)蒙古化的突厥部落。
其一是克烈部,又稱“怯烈部”“凱烈部”或“客列亦惕”,是蒙古部興起前蒙古高原人口眾多、勢(shì)力強(qiáng)盛的重要部落。據(jù)說(shuō),克烈部過(guò)去有一個(gè)首領(lǐng)的七個(gè)兒子膚色全為黑色,故取名。其主要部落有六支——客列亦惕、只兒斤、董合亦惕、土別兀惕、阿勒巴惕、撒合亦惕。克烈部的駐牧地主要分布于肯特山和杭愛山之間的鄂爾渾河和土拉河流域,金朝初年已建立相對(duì)獨(dú)立的游牧政權(quán),接受金朝的冊(cè)封。金朝中期,給鐵木真巨大幫助的克烈部首領(lǐng)汪罕,就是被金朝冊(cè)封為王的,后來(lái)也接受耶律大石建立的西遼王朝的羈縻統(tǒng)治。克烈部的部落首領(lǐng)常采用突厥語(yǔ)的名字或稱號(hào)。克烈部占據(jù)著回鶻汗庭故地游牧,信奉佛教和景教。
其二是乃蠻部,《遼史》稱“粘八葛”,《金史》稱“粘拔恩”,是遼金宋元時(shí)期蒙古高原西部著名的大部落。乃蠻部被西遼長(zhǎng)期統(tǒng)治,其王子屈出律以女婿身份篡奪了西遼皇權(quán),其岳丈西遼懷宗耶律直魯古為太上皇。屈出律后被西征之蒙軍追殺,西遼遂亡。
元明以后,乃蠻部逐漸融入其他族群,在克烈部以西游牧。
其三是汪古部也稱“瓦克”“雍古”“王孤”“甕古”“旺古”“汪骨”“汪古惕”,遼金元時(shí)期陰山以北部族。拉施特在《史集》中說(shuō),金朝皇帝為了防御蒙古部、克烈部、乃蠻部等部,修筑了一道大墻叫“汪古”,交給該部族守衛(wèi),該部族因此而得名。
元明時(shí)期,汪古部大部跟隨乃蠻部和克烈部西遷,少量留在原地,被漢人同化。汪古部人信奉景教。他們皮膚白皙,性情溫和,文化水平很高,深得金廷信任,金廷特地安排他們游牧于陰山一線,形成對(duì)漠北游牧族群的一道屏障。
塔塔爾部是一個(gè)強(qiáng)盛的部落,他們以好動(dòng)刀子而著稱,天性中充滿了仇恨、憤怒和忌妒,與人口很多的蒙古部經(jīng)常為草原、水源、牲畜、嫁娶等發(fā)生戰(zhàn)爭(zhēng)。
金朝初年,蒙古部已成金廷藩屬。金太祖時(shí),為防范北阻卜等北方游牧族群,金廷下令婆盧火部在泰州[10]屯田以戒備。金太宗曾宴請(qǐng)游牧諸部,喝得酩酊大醉的合不勒汗[11]竟然不顧正規(guī)禮節(jié),去捋金太宗吳乞買的胡須,幸虧吳乞買高興而未加責(zé)罰。
金熙宗、海陵王時(shí)期,蒙古部與塔塔爾部都是高原東部著名的大部落,都向金廷稱臣納貢,并被授予類似中原州縣級(jí)別的軍政職務(wù)。塔塔爾部在表面上更加親近金廷。
合不勒汗擔(dān)任蒙古部領(lǐng)袖時(shí)期,其妻弟賽因的斤因患病,請(qǐng)塔塔爾部的薩滿巫師施行巫術(shù),不料,非但沒(méi)有治好病,反而一命嗚呼了。賽因的斤的弟兄一怒之下,殺死了塔塔爾部的巫師。從此,塔塔爾部同蒙古部結(jié)怨。雙方經(jīng)常發(fā)生屠殺和搶劫的事件。
蒙古部雖為金朝藩屬,但到合不勒汗當(dāng)政時(shí)期,已經(jīng)有所發(fā)展,也有擴(kuò)張的意識(shí),經(jīng)常襲擾金朝州縣,引得金軍一次次進(jìn)行征伐。金軍多次征伐得到塔塔爾部明里暗里的幫助,但是,金軍主要戰(zhàn)斗方向在南方,不會(huì)投入重兵進(jìn)剿蒙古部,而女真人并非游牧族群,不擅長(zhǎng)大漠和戈壁地形下的作戰(zhàn),故合不勒汗帶領(lǐng)蒙古部成功抵御了金廷的數(shù)次軍事攻擊。金熙宗曾派金兀術(shù)(完顏?zhàn)阱觯12]領(lǐng)軍八萬(wàn)北征,與蒙古部以西平河為界。海陵王曾派西京路統(tǒng)軍調(diào)集四路人馬北征,也未達(dá)到蕩平蒙古部的目的。
以南方為戰(zhàn)略進(jìn)攻主方向的金廷無(wú)暇北顧,也認(rèn)為不值得對(duì)北方這些“一打就跑”的“蠻夷之人”費(fèi)心費(fèi)力,所以采取中原王朝慣常使用的冊(cè)封和厚賞——“冊(cè)其酋長(zhǎng)熬羅勃極烈為朦輔國(guó)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于是熬羅勃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數(shù)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jù)要害而還”[13]。這事發(fā)生在金熙宗時(shí)期。
看來(lái),合不勒汗時(shí)期,蒙古部表面上保持著臣子身份,但已經(jīng)敢與金廷分庭抗禮了,并利用金廷不能徹底剿滅自己的現(xiàn)實(shí),不斷挑釁,逼迫金廷給予豐厚的“賞賜”。
或許為平息蒙古部和塔塔爾部之間長(zhǎng)期的沖突,合不勒汗的堂弟俺巴孩,剛剛擔(dān)任部落聯(lián)盟長(zhǎng),就答應(yīng)將女兒嫁給塔塔爾的一個(gè)部落首領(lǐng)。俺巴孩與合不勒汗長(zhǎng)子斡勤巴兒合黑護(hù)送其女兒出嫁時(shí),被塔塔爾人抓住并送往金廷。俺巴孩托人告訴部族,要替他報(bào)仇。金熙宗將俺巴孩等人釘在木驢上處死。據(jù)說(shuō),這是金廷專門懲治游牧叛人的刑罰。
半個(gè)世紀(jì)后,鐵木真成吉思汗在討伐金廷之前,在祭天儀式上發(fā)誓為祖先俺巴孩等人復(fù)仇。

